|
|
嘉偉德著 林昌華譯 《十字架下的教會:亞洲激盪時期的宣教,第一卷》譯自Karsen,Wendell Paul,1936- “The Church under the Cross: Mission in Asia in Times of Turmoil”Pub.by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v.1 June 2010, Page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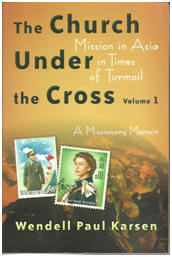 簡介 簡介
主後2000年,標記著一個千年的結束,也是我在亞洲30年宣教師生涯的終結。我和妻子任絲嘉(Renske)搭機從印尼回到紐約市,我們將在那裡舉行的「美國歸正教會」(Reformed Church of America)總會期間宣告退休。當我們的飛機降落甘迺迪機場時,我的思緒回到了1969年12月的某一天。當時,我帶了三個年幼的孩子,和當時的妻子喬愛斯(Joyce),也在同一個機場搭機前往一個對我們來說極端陌生的所在。我們飛越半個地球前往亞洲,那是一個神秘的地方,我們對那裡的瞭解完全透過宣教師的描述,和通過書籍、相片和地圖的「眼見」的粗淺印象。更精確來說,我們旅途的終點站是「台灣島」,以及那裡的1,600萬居民,那裡是我們接受呼召前往服事的所在,而那裡的居民是我們期盼能分享基督教福音信仰的對象。
根源 (Roots)
整個故事要從伊利諾州的芝加哥開始談起,我在1936年出生。我的雙親希伯特和馬格列.卡森(Siebert and Margaret Karsen)以他們自己生命經驗為典範,鼓勵我將自己奉獻給基督使用。他們安排我到「基督歸正教會」(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所辦的「提摩太基督文法學校」(Timothy Christian Grammar School)和「芝加哥基督高級中學」(Chicago Christian High School)。除外,當他們在「基督歸正教會」的「好幫手佈道團」(Helping Hand Mission)音樂佈道,或是帶領「太平洋花園佈道團」(Pacific Garden Mission)前往芝加哥的貧民窟(Skid Row)主持禮拜時,也常常帶著姐姐南茜(Nancy)和我一起前往。甚至在特定月份的週日下午,當他們受邀福音廣播而前往地區的廣播電台演講時,也會帶著我們一起前往。由於我的母親多年參與「基督歸正教會」在芝加哥對猶太人佈道的團隊「拿但業協會」(Nathanael Institute)的服事。所以在暑假期間,我常常整個下午陪伴她在街道上的佈道車裡,而那裡常有猶太人婦女前來參加「查經班」或團契活動。偶而我的雙親也會參加傍晚的佈道會節目,而我和姊姊也要陪伴參加,而陪坐在觀眾席裡。通過這些經驗,讓我年幼時期就體認到將基督福音分享出去的重要性,而且很樂意與那些和我極不相同群眾互動。
我的雙親也協助希瑟羅市「第一基督歸正教會」 (First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of Cicero)設立「宣道委員會」(Mission Committee)。因此,經常有外派的宣教師來到家裡拜訪,譬如:奈及利亞的Bena Kok,錫蘭(斯里蘭卡)的John and Clarence van Ens,奈及利亞的Rolf Veenstra,中國的Everett and Rose van Reeken以及其他許多宣教師。我和姊姊常常從這些訪客口中聽到遙遠地區的奇異風俗、陌生的動物、扣人心弦的事件、令人嚮往的風景、以及認識從來沒有聽過福音信息的人群。他們述說的故事常讓我們張大嘴巴,錯愕不已。此外,我們的雙親也鼓勵我們閱讀紀錄著宣教師傳奇,或為福音犧牲偉大故事的兒童書。讀到這些文字,在我幼小的心靈投下震盪的浪花。當時童稚的心裡想著,或許將來我應該也要當宣教師吧!
然而,讓我認真思考成為宣教師的想法,反倒是來自1940年代所有孩童都會緊緊黏住耳朵不放的一個廣播節目,這個節目叫做《戴瑞與海盜》(Terry and the Pirates),而故事的場景就在香港。在童稚的腦海裡的香港是個混雜著異國氣味、神秘的風俗習慣、奇異的風貌、神奇的冒險、以及對我來說極端陌生中國人的所在。我的名字Wendell 的意思是「流浪者」或「探險者」,而我的人生經歷就如同名字所標示的,我前往許多神奇的地方,如香港,而在服事主的時候經歷一兩次奇異的冒險。不管如何,在我進入青少年的時候,我的跨文化宣教也在我的心裡頭開始滋長。
災難 ( Trauma)
1954年9月時,我的生命發生劇烈的改變,就剛結束依利諾州惠頓學院 (Wheato College) 第一天的課程,參與了學長學姐的歡迎會之後,在我步行回家的路上,災難發生了。當時惠頓市正在興建新的自來水系統,我經過的道路設置著路障,但是黑暗的人行道上並沒有任何標示。突然間我跌落15呎的深溝當中,當我的腳撞擊溝底的水泥地時,像是牙籤一般折斷了。我痛苦的哀號,但是沒有辦法移動身體。我呼喚上帝的幫助,而祂聽我的呼求。
在這個時候,我最要好的朋友史高特.奧略(Scott Oury)剛好開車從路口經過,停下來等候變燈。他聽到我的呼叫聲,走出車子,然後細心的走過黑暗的人行道,趴下來從深溝邊緣往下俯視。從黑暗的洞口我認出他的臉來,趕緊大聲叫著他的名字,驚駭之餘的他從人行道邊爬下,來到我的身邊,而其他的人趕緊跑去救火隊尋求幫助。
在經過一段痛苦的等待之後,救火隊員終於來到,在經過一段時間���嘗試之後,才將我由深坑救出送上救護車。稍後,醫生告訴我,如果我在坑洞當中多待數個小時,我可能會因驚嚇而死亡;然而,上帝對我有別的安排。
之後,我經過一段時間的試煉,在一個月的住院期間,我經歷兩次的開刀,也失去30磅的體重。就在受苦的那段時間,有許多人不住的為我禱告,幫助我順利通過一整個月的身體復原,讓我在第二學期一開始的時候,順利的返校復學。
在那段時間,我開始對一切的醫療過程和醫生、護士的職業生涯產生興趣來。事實上,我的姊姊南茜正在接受護理師的訓練。在忽視了上帝賞賜的天賦,以及醫學這個艱困學科所需的高分成績和量化分析能力之下,當時的我決定要擔任一位醫療宣教師,就像亞伯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一樣。
新發現 (Discovery)
我在惠頓學院的求學經驗,增強了我對宣教工作的興趣。在惠頓學院裡,我們接觸許多來學院拜訪的跨文化的宣教師。他們提高了上帝的呼召的聲音,也讓我們意識到這個世界急迫的需求。也在那段時間當中發生惠頓畢業生Jim Elliot, Nate Saint 和Ed McCully,以及另外兩位宣教師在厄瓜多爾殉難的事件。這個發生於1956年的不幸事件對學院帶來巨大的打擊,也衝擊了學生和我對海外宣教的興趣。惠頓學院最主要的建築物牆壁上,列舉了數百名回應上帝呼召而擔任海外宣教師的惠頓畢業生名單。
足足花費4年的時間,上帝(和科學系所)才讓我瞭解,儘管有擔任宣教師的恩賜,但我不會成為另一位史懷哲。由於學業成績不錯,所以從學院獲得科學學士的學位,但是我科學科目的成績還沒有優異到可以去申請醫學院的入學許可。但我並不氣餒,於是申請普渡大學動物學系的碩士班而得到接納,我以為那是將來進入醫學院的偷渡口。
但是,就在那個時候,我的生命經歷另一次的轉變。當我還在惠頓的時候,我參與數個基督徒的活動,包括成為學院四重唱的一員。由於數年前的四重唱團曾經參與惠頓學院詩班前往歐洲進行7週的巡迴佈道演唱。所以四重唱的同伴和我有一個想法,那就是在畢業的暑假前往歐洲進行佈道演唱。儘管,詩班代表學院,但是我們的旅程安排和經費都必須自己準備。有一位演奏伸縮喇叭而即將前往牧會的畢業生與我們同行,他負責演奏鋼琴,因此整個團隊增加到6個人,包括:Paul Groen 低音,Russ Bishop 中音,Jim Ferris 第一男高音,我第二男高音,Emery Cummins 鋼琴,John Herzog 佈道,而我們將團隊命名為「福音詠嘆隊」(Gospel Aries)。我們的想法是前往歐洲鄉間,協助當地的牧者對青年人進行佈教的活動。
由於擔任整個團隊的秘書,我負責安排演出活動,宣傳,以及負責財務方面的規劃,這是整個佈道團隊活動中,屬於比較實際和細節的部份。結果是我們在70天的巡迴時間前往愛爾蘭、英格蘭、蘇格蘭、法國、比利時和德國,進行了90場的演出。我們當中有一流的摔跤選手在牧師館前進行表演,藉以吸引青年的注意,進而邀請他們參與傍晚的佈道會。我們也進行逐家探訪佈道,海邊佈道,以及其他各式活動鼓舞群眾參加。經過這次的經驗,我開始發現自己有這方面的恩賜:與青年人一起工作,分享福音信息,領唱,安排活動和後勤事務的安排等。也體認到,暑期的佈道之旅,實在是「跨文化宣教」最好的訓練機會。
這個時候我才真正體認到,我應該是去神學院而非醫學院接受造就。暑假的經驗讓我看到另外一個可能性,但是這些事我自己的想法,還是上帝的安排?我決定學習「士師」基甸的作法,先告訴上帝,將追求醫療宣教師的夢想延後一年,而前往神學院接受一年的神學造就,然後再來看「醫學」和「神學」當中,哪一樣才是我的人生目標。
命運 (Destiny)
回到美國之後,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申請惠頓學院的神學研究所(Wheaton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那是一年期的神學預科訓練。當我的申請獲得接受之後,我立刻通知普渡大學已經改變主意,不前往該校修習動物學研究所了。就在我申請惠頓神學研究所的時候,我遇到一位後來成為我妻子的年輕女性喬愛斯.休斯(Joyce Hughes)。而就在惠頓那年當中,我越來越覺得我的恩賜和興趣應該是往神學院的方向走才對。我更覺得喬愛斯和我是互相所屬,而且我們一起前往海外擔任宣教師應該會很適合才對。很幸運的,喬愛斯也逐漸和我有相同的想法。
會讓我們產生共同結論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在週末時一起參加芝加哥南邊,非裔美人貧民區域的佈道計畫。通過主日學的教導,和逐家的探訪佈道,我們算是嚐到了跨文化宣教師的滋味。而且我們也覺得有對方的陪伴,一切都很自然。於是在1959年5月我們訂婚了,並於1960年6月結婚。在那段時間,我們經歷3次痛苦的別離。1959年9月,當我前往加州巴薩迪納 (Pasadena) 的富勒(fuller)神學院進修時,喬愛斯留在惠頓學院繼續新約學的碩士課程。我找機會在三次的假期中溜回惠頓學院陪伴喬愛斯,但是我們大部分的聯絡都是透過書信往來,電話實在太昂貴了。
觀點 (Perspective)
我在富勒神學院接受了扎實歸正教會觀點的教育。我對跨文化宣教的興趣也通過普世宣教與福音的課程,以及接觸一些來訪宣教師在教堂的演講和課堂討論而加深。我在那裏接受的堅定神學基礎,以及神學院對海外宣教的熱衷,加上普世的關懷,都讓我在牧會與宣教的服事上堅定腳步。喬愛斯與我在富勒第一年結束時結婚,在後來兩年中於富勒所在地的巴薩迪納一起生活。富勒並沒有加深我們對跨文化宣教的熱情,但卻改變了我們的觀點。Clarence Roddy博士是我實踐神學課程的教授。有一天,他在課堂上講了讓班上同學震撼的一段話。他說:「如果你們想要成為海外宣教師,那麼就應該先將福音的信息傳給與自己同文化的同胞吧。」喬愛斯和我為此一起討論,也為此祈禱很長一段時間,最後我們認為老師的話沒有錯。到目前為止,我還是認為他是對的。於是我們決定在研讀神學碩士班期間,先終止海外宣教的想法。然後將全部精力集中於訓練自己的青年宣教、講道、教牧關懷、教導、佈道、協談、行政事務,以及其他101���,在教會導入幹事制度以前,牧師必須具備的能力。
轉換 (Transition)
在那段時間,我們的會籍仍屬於基督歸正教會。在參與富勒神學院那段時間,我在洛杉磯第一基督歸正教會擔任主日學的輔導,也在洛杉磯地區的基督歸正教會負責主日講道的服事。在富勒神學院最後一學期,我申請位於密西根州大河灣市(Grand Rapids)的「加爾文神學院」(Calvin Seminary)的神學碩士班就讀,為將來在基督歸正教會受封牧作準備。然而,由於我先前在一間跨教派的神學院受造就,因此加爾文神學院要求我必須先修習2年半的神學課程之後,校方才會考慮是否願意接納我進入神學碩士班就讀。就算完成學業,我還必須通過6個委員會和法規會的審核後,再經大會(Synod) 給予特別的授權,才有資格被封牧。遭遇這些困難,我的人生面臨巨大的阻擋。
我是在基督歸正教會長大成人,但是我的母親全家都是屬於美國歸正教會(Reformed Church of America)。在我的孩童時期,我常常在親戚的教會(希塞羅市西邊歸正教會)做禮拜,參與假日聖經學校,以及其他許多的活動。雖然我的母親嫁給父親後就參與父親的教會,但是她從來沒有失去對歸正教會的情感,也一再對我們述說曾經參與過教會活動的美好經驗,以及對所屬的哈士丁街教會(Hasting Street congregation)的感情。念神學院之後,我逐漸體會到基督歸正教會(CRC)與美國歸正教會(RCA)兩個教派間在心態上、社會見解、普世教會觀點、宣教概念、以及神學上細微的差異之處。
經過長時間思考、討論、和祈禱之後,喬愛斯與我決定,應該考慮將來在美國歸正教會受封立牧師的可能性。而位於密西根荷蘭市的威士登神學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對我探詢的回應,實在是極大的鼓舞。他們歡迎我立刻進入神學研究所的課程,並建議我修習幾門瞭解這個教派的課程。除了這個之外,他們唯一要求,是我必須參與幾次為非歸正教會神學院畢業生舉辦的神學考試。在通過考試以後,我將會獲頒「專業證書」(Professional Certificate),而這個證書將讓我得以在「荷蘭大會」(Holland Synod)受封立,並且得以在歸正教會所屬的堂會牧會。而在那個時間的1962年6月23日,我們在富勒歡迎長子司提反.約翰(Stephen John)的誕生。
封牧 (Ordination)
要作決定並不困難,1962年我們就來到荷蘭市。在那裡我遇到了宣教學者John Piet 博士,他有許多年的時間在印度擔任宣教師。透過他我得以了解歸正教會的宣教歷史以及教會目前的宣教情況。我很意外發現,小小的一個宗派,竟然在過去200年間對世界宣教事業有巨大的影響。在當時我也發現,當時還有150位宣教師與11個國家的普世教會機構合作,建立或支援地方的教會。因此,我感覺到自己來到歸正教會並非偶然。因為對這個教派的親密感覺、它的宣教哲學與政策是我所深深認同的。
在那一年當中,我參與校方為我安排的課程與考試。而我們的講道學教授Henry Bast博士在12月的雪夜來到我家探訪,之前他在密西根州大河灣市的伯大尼歸正教會(Bethany Reformed Church)擔任牧師,他來邀請我擔任助理牧師的工作。這對我來講是個極好的經驗,因為嚴格來講,我在這個教派算是新人,並且大致上也了解,在那一年幾乎所有的教會都已聘完神學院畢業生。伯大尼教會是一間很大的都市教會,所以能夠提供我各種場域的牧會經驗,由於Bast博士是歸正教會的放送牧師(radio minister),因此必須經常外出佈道,而讓我負責教會的事務。除此之外,伯大尼教會也是間具有宣教意識(mission minded)的教會。教會的先輩Gordon van Oostenberg博士,鼓舞教會通過宣教計畫,宣教會議、和支援數位美國歸正教會跨文化宣教師的需要,而負起這個世界需要的責任。我很樂意接受這個邀請,於是在1963年1月份起,我以半職的身份在那裡服事,直到5月完成神學院的課程和通過考試為止。之後,我通過荷蘭中會(Holland Classis)的考試,然後封牧受差派前往伯大尼教會牧會,而在7月13日起成為該教會的助理牧師。那一天對我來講,實在是生命中極為愉悅和感動時刻。愉悅的是,因為我擔任牧職的呼召終獲確認,而且我的牧會恩賜也得到確定。另我感動的是, 我有機會服事有需要的人,而且可以訓練我的能力,以便將來能夠在異文化的人群中使用。
儘管大部分的時間我負責的對象是青年人,但是,我還是必須擔負培育教會宣教使命的異象。這意味著,協助假日聖經營和主日學計畫和推廣宣教會議,組織宣教計畫,以及接待歡迎宣教師來教會演講分享。也就是在伯大尼教會讓我們和退休宣教師譬如台灣的羅慧夫醫生夫婦(Sam and Lucy Noordhoff),衣索比亞的Margaret Doorenbos,蘇丹的Bob and Morrie Swart等人建立密切的關係。我也必須負責教會周邊地區的佈道會。我們在伯大尼教會服事期間,次子腓利.西伯(Philip Siebert)也在1965年6月9日誕生。
牧會生涯 (Ministry)
1965年秋天,密西根州威克斯堡 (Vicksburg) 的「湖邊地歸正教會」(Lakeland Reformed Church)前來邀請我過去牧會。我接受他們的邀請,因為這間教會的社區的事工的能力很強,因為它們的會友來自各宗派,因為它提供我獨立牧會的機會。在那裏,我必須在繁忙的教導,講道,青年工作,探訪,協談,和行政事務之餘,找時間完成我的碩士論文,《保羅有關連結於基督的教義》 (Paul’s doctrine of union with Christ)。這篇論文終於在1967年完成,而讓我成為美國歸正教會貨真價實的畢業生。
整個過程也讓我學到學院研究的訓練。幫助我增進寫作的能力。這兩種能力的訓練在將來對我的幫助超過我所預期的程度(特別是先前,我的英文從來沒有得過好成績)。
在湖邊地教會期間,我採取以宣教意象主導(mission-focused vision)的牧會模式,在每一年秋天,教會舉行一個禮拜之久的「宣教節慶」,除了邀請宣教師的演講以外,我也挑戰會友對歸正教會的宣教工作做出貢獻。退休的宣教師,如台灣的Ted and Harriet Bechtel,巴基斯坦的Paul and Dorothy Hostetter,肯亞的Harvey and Lavina Hoekstra以及台灣的益士德夫婦(Rowland and Judy van Es)都成為我們的朋友。我們也舉辦目標明確的「在地宣教」(Mission at home),對象為教會週邊的社區,因此教會附近的居民願意委身於耶穌基督,而加入我們的教會。在此同時,我發現對大學年級的青年宣教產生興趣,而這個興趣在將來於海外服事時成為我全時間的服事的核心。而在這段時間,我們第三個孩子林拉潔(Rachel Lynn)也在1968年4月21日誕生。而那一年是我們在湖邊地教會10週年紀念。
決定 (Decision)
在湖邊地教會服事期間,我和喬愛斯覺得,參與宣教而到世界另一邊的想法越來越強烈。歸正教會派往衣索比亞的宣教師Bob and Morrie Swart 是我們教會1968年秋天宣教節慶 (mission conference) 的主題演講者。在他們生動的演講之後,當天晚上在我家過夜,當晚與我們分享他們宣教地的景況,以及作為跨文化宣教師是什麽情況。而我們也分享長時間以來對海外宣教的興趣。聽完之後,他們建議我立刻去向美國歸正教會「世界宣教委員會」(Board of World Mission)申請擔任宣教師而不要遲延。於是,我們一起禱告,而喬愛斯與我決定在當晚就着手進行。我們並不確定是否會被接受,但是我們決定牧會的訓練已經完成,因此願意貢獻所學。
再過來的問題是,何時?何地?先前兩個月與惠頓學院合唱團以及學院福音隊兩個月歐洲的經驗,我們以為歐洲應該是最適合我們服事的地點。但是我們也認為應該讓歸正教會決定何處最需要,然而我們還是認為不論如何,應該還是會在歐洲的某處。而我們唯一的條件是,我們不願意去必須將我們三個小孩送往寄宿學校的任何地點。經過數個月秘密的協調之後,我們很高興得知,申請已經被世界宣教委員會接納了,而我們必須開始準備在1969年6月的新任宣教師訓練課程。
任命 (Assignment)
但是讓我們感到意外的是,歸正教會通知我們,最適合我們恩赐的地點是亞洲,更精確的說是台灣的校園福音工作(campus ministry work)。我們對亞洲幾乎沒有���何概念。對我們來說,那是個充滿神秘,甚至是不友善的所在。一個喚起童年所閱讀《戴瑞與海盜》(Terry and the Pirates) 故事的地點。亞洲文化對我們的實際經驗甚至是閱讀經驗來講,都是光年以外遙遠的距離。他們的食物看起來奇怪、他們的語言似乎難以理解、他們的風俗也看起來古怪、他們的藝術看似怪異、而宗教則是奇特、而這樣的例子可以列成長長的一整串。但是,呼召終究還是呼召。有許多時候在講道之時,我不是提到上帝叫我們去做困難,令人不舒服的事情時,一定會裝備我們有能力去完成它嗎!現在正是將講道內容付諸實行的時候了。於是,我們通知教會將會去赴任。
從正面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朋友羅慧夫夫婦,Ted and Harriet Bechtel 以及益士德夫婦(Rowland and Judy Van Es)不也都在台灣服務嗎?而且校園福音工作對我們來講很有吸引力。我們立刻寫信給他們詢問上百個有關生活與服事的問題。然後我們開始閱讀可以入手有關亞洲,中國或台灣的任何資料或書籍。而世界宣教委員會秘書回答我們問題,關於歸正教會合作的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事情,也告訴我們實際層面的問題,譬如我們5人的家庭要如何到達那裏,將會住在哪裡,以及我們需要帶什麽過去等等建議。
犧牲 (Sacrifice)
當然,我們同時也將計畫告訴家人,在得知我們對跨文化宣教的興趣,並且也認為這是最高的呼召之後都非常的支持。當被告知整個計畫發展的狀況時,他們並不感到特別意外;然而,當得知這個計畫已經確定之後,他們內心不免感受到沮喪與刺痛,因為他們的孫子將遠離到地球的另外一邊,而且只有每隔4年才有機會見到他們一次。這也我我們一再衡量的問題。
作一名宣教師有許多必須犧牲的所在,事實上,我們真正的犧牲就是遠離親人那麼長久的時間。但是,從另外一個觀點來講,那些宣教師的先鋒們,是每隔7年才有回家的機會,而當中有些人是連一次都沒有回去過。當我們接受這個呼召時,新發明的噴射客機,不僅讓人能夠有更多的機會回去(若有緊急的狀況),也可讓雙親前往探訪,而那種方便的情況是幾十年前根本無法想像的。但是,終究會有一天,距離會讓宣教師的家庭面對困難的情境。譬如,某位親愛的姨母過世,等到你終於有休假機會可返鄉時,她早已毫無蹤影可尋。或者當孩子長大必須回去已成異文化的故鄉入大學,擔任宣教師的雙親,則必須在雙腳顫抖不停代禱的情況下送走他們。但是這對當時的我們來講,還是遙遠的未來。
問題 (Questions)
最後,也是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告訴湖邊地教會的會友牧師即將遠離的事實。我們不想在情況還沒有明朗的情況下,就讓會友知道我們尋求擔任海外宣教師的機會。因為,如果沒有如預期的成果,我們還是必須回去教會繼續牧養的服事。我們愛湖邊地教會的弟兄姊妹,而這種情感是互為影響的。現在時機已到,必須告訴會友,我們不只要離開,而且是要前往台灣。我利用春天的會員大會時宣布這個訊息。但是,會友的反應卻是相當的複雜,他們拍掌鼓勵我們願意外出擔任宣教師的信念,但是他們也為了我們所作的決定,對他們的影響感到失望。在會議結束之後,一些女士(她們很喜歡我們的小孩)紅著眼眶跟我走進辦公室:「你們怎們狠心將小孩帶到如此遙遠和奇怪的地方!遠離自己的文化,家人和玩伴,他們將怎麼辦!」
這樣的煩憂也算合理,我們將如何處置這些小子呢?我們不斷思考這個問題,也為此不斷的禱告,因為我們做了一個會永遠改變他們命運的決定。我們只在意自己的「使命」,而忽略他們可能會遭遇的困境,這樣對嗎?我們除了確信不管在世界的什麼地方,上帝會也一定愛他們、保守他們、養育他們的信心以外,他們在幾年之後的回應,應該是可以清楚的回答這個問題才是。在第4個小孩安得魯(Andrew)在香港誕生,成長到7歲的時候,我們討論可能必須回美國以便照顧最年長的兩個孩子。「但是,媽媽、爸爸!」他們抗議道:「你們怎麼可以在這個時候回美國?這樣安得魯就沒有機會像我們一樣在亞洲長大了。」
其他的人也大聲提出質疑,為什麼我們在本地的國民還有需求的時候,跑到國外去服事。這是另外一個我們思考和禱告很久的問題。對這個問題,比較從信仰的角度來的解答是,第三世界 (third world) 的國家有更大的需要,因為在那裡只有少數的基督徒,因而相對來講,極度欠缺服事的人。而比較從人性角度的回答是,因為在「那邊」的跨文化戰壕裡,比在生活與工作在自己的後院中,有更多意料外的挑戰,更多的機會,更多的探險,更多的發現。第一個解答讓人容易理解,而第二個解答則是讓人睜大眼睛。
洗禮 (Baptism)
六月來了,我們卻要離開。我們打包少數生活用品裝船送往國外,將大部分的家庭物品以一整天拍賣會的形式處理掉,透過拍賣我們獲得1,100美元的收入,作為到達台灣之後新家支出的基金。之後,我們前往紐約的Stony Point的宣教師訓練中心。這個中心擁有哈德遜河邊美麗的環境,是一個跨教派的宣教師訓練中心,由幾個主要的教派合作支應經費,提供服務人員,以及場地的運作。合作教派中也包括美國歸正教會在內。我們做夢也沒有想到,在中心5個月的時間,我們被拉出從小成長,受教育和工作的舒適與保守的蟲繭之外。
首先,1969年是學生反抗運動最高潮的時期,在當年暑期在那裡受訓的100名學員和45名孩童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學生運動者,他們期望前往國外去探險,透過教英文、或某種形式的社會工作,而由教會支付開銷。不少人公開反對教會、基督教傳統和信息。而像我們這種對教會委身、支持基督教傳統和信息的人,就會被稱作是「打領結的人」(wore the collar)。學生挑戰營地的服務人員,要求將重新調整已經安排妥當的節目。強調以「參與者平等的民主制度」(participatory egalitarian democracy)作為整個節目安排的原則。不接受訓誡、不接受書本、採取小組討論(T- groups)的原則,挑戰所有的權威。質疑我們對其他文化和信仰傳揚福音的動機。對我們來說,那叫做「烈���的宣���洗禮」(baptism for mission by fire)。
然而,這個起初看起來似乎悲劇(travesty)的開頭,卻是我們所能想像,對非基督徒文化宣教的最好訓練課程。就在眼前,是試驗我們如何服事和我們極不相同對象的機會,去向那些帶著懷疑的人說明我們的信仰,去向那些嘲笑的人展示基督徒的愛。最後,那些曾經出現的阻擋被耐心突破了,那些剛離開校園自許為「革命份子」(revolutionaries) 的人,終究只是一個普通人而已,他們也有一般人的懷疑、期望、恐懼和需求。
當這群人在訓練結束離開之後,我們比較年長的家庭總算可以鬆一口氣,在接下來的4個月的受訓過程,我們可以在一個比較正常的氣氛下進行。但是,我們多少會想念這些年輕人,他們教導我們看到自己,他們讓我們重新思考自己信仰的深度,讓我們以較寬廣的眼光來看社會,然後以先前從來沒有被挑戰或練習的機會的方式來表達愛。他們有許多人也被改變。他們學會尊重我們,對我們的基督教信仰感到興趣,傾聽我們觀點的基督徒生活,以及欽佩我們對傳福音的動機。我希望那年夏天所播種的種子能夠在海外推動「使命」時,能發出信心的芽出來。
延伸 (Stretching)
對我們這些在基督歸正教會當中成長,在福音環境下受教養的人來講,有一些比較次要但仍困難的調整之處。聖餐時採用吉他和民謠的方式,實在很奇怪。由婦女主持聖餐則是更加奇怪。各樣的新觀點挑戰我們保守的宣教觀,福音觀,上帝國概念,教會觀,以及其他的議題。我們的腦海裡也浮現出許多問題來。譬如:我們要如何在一方面尊重其他文化,但在另一方面卻要改造他們的文化?我們要如何與其他信仰的人接觸?我們這些外國宣教師要如何與政治上和經濟上有系統推行不公義政策的統治者連結?我們要如何在種族主義的社會中,真正的學習去愛和接納那些有色人種,以及文化上與我們極度相異的人?而共和黨,或其他政黨對那些議題的看法,與上帝國的差異在哪裡?
演講主題中,討論福音與公義在政治、經濟、社會、以及生態上的議題,讓我們暴露在過多的難題當中,也是早先我們極少接觸的環節。而在紐約東哈林區的聯合住宅(Union Settlement House)以及附近的貧民窟所進行的「跨文化接觸行動」(cross cultural venture),讓我們直接面對要「改變世界」是多麼困難的事實。語言的課程讓我們去面對學習外國語言的困難,而對我們來講,那就是巨大的中國文字。
在上述的課程之外,是我校園福音工作的特別訓練,因為那是我在台灣將要負責的事工。我被要求去調查紐約長島上三個校園福音工作的模式。一個是傳統學院的環境;一個是「漂浮」(floater)模式,亦即同時在數個校園進行福音工作的模式;而一種是在州立大學的模式。我被分配的作業,是吸收和評估這三種模式當中,校園福音工作是如何進行的,然後將我的發現調整運用在台灣的大學環境裡
。
在這當中,紐約大學在Stony Point的校區,是最具挑戰性的作業。這裡UNYSB被公認是美東的加州柏克萊,也是美國東岸學生反抗運動的大本營。在校園的8000名學生中,我的調查發現65%為猶太教徒,30%為天主教徒。而其他的學生的宗教信仰,從禪宗(Zen Buddhists)、到「山達基」(Christian Science)的信徒都有。那裡沒有「宗教對話中心」(interfaith center),沒有全時間的校園牧師,也沒有宗教系所。而最著名的教授,就是引領「神死神學」(death of God)的神學家Thomas Altizer,在三個月當中,我每週往來於「訓練中心」和紐約大學之間數遍,經常至少一個晚上留在特定的校園裡。我也曾經以一個禮拜的時間住在讓大開眼界的紐約大學宿舍裡。我訪問具有代表性的校園人物,包括校園牧師、教授團的職員、以及學生都有,也從校園的小組和活動當中採集樣本。
有一天晚上,我去參加紐約大學學生的「民主學會」(Democratic Society)所舉行的會議,會議的目的,是向冷眼旁觀的150名學生和一位和激情的宣教師解釋這個組織,他們說組織長期的目標,就是聯合學生和工人透過武力來推翻這個國家的「帝國主義統治階層」,建立馬克斯、恩格斯和列寧所規劃的共產主義國家。他們的計畫就是透過宿舍的細胞、書桌、遊行、罷課、辯論等手段,將影響力擴充到全校園。這些群眾相當冷漠,更不用說這些養尊處優的年輕人從來不曾工作過,竟然有解決整個社會病態的藥方。而且不遲疑的譴責任何不同意他們的人。
在群眾當中的我,由於年紀、服裝的不同,加上不斷書寫筆記,引起他們的質疑。突然間,一位學生站起來,要求我表明身份。我向他們解釋我是一名基督教牧師、正在接受校園福音工作的訓練,並將前往台灣工作。但是,這個解釋對他們來講,無法理解。「你是聯邦調查局的告密者!」,他們大聲喊叫,我自作冷靜,但是會議在混亂中結束,有人前來騷擾我,於是我離開會場,並且懷疑將來在台灣的校園工作,是否會遇見相同的景況。
啟程 (Launch)
12月初,我交出校園福音工作的研究報告,於是這門課程算是結束。接著在歸正教會的紐約總部接受任命,然後我們打包行李。我們訓練課程已經結束,現在必須去面對真實的世界—也就是在數年前所規劃的異象。我們向那裡告別,也向那裡所愛的人群辭行,包括職員、我們的教師、新朋友以及同工。我們在紐約甘迺迪機場開始漫長的旅途,中途停靠南卡羅來納的Greenville,接著就是伊利諾州的芝加哥,去向我們的親人和朋友道別。然後下個目標就是台灣,旅途中我們強烈感受到上帝一路的陪伴。
快轉 (Fast Forward)
30多年後,我再度來到我們所愛的Stony Point宣教師訓練中心,這裡已經改名為「Stony Point Center」,中心的執行的計畫仍然集中在國際跨文化的議題,但是已經沒有宣教師在這裡接受訓練。我走過營地進入大廳,那裡曾經是盈滿著歡笑聲、辯論聲,以及新任宣教師孩童的吵鬧聲。1969年和我們同在那裡受訓同伴的臉孔快速在我的腦海浮現。我好奇,他們現在都在哪裡了?他們的海外宣教服事結果怎樣呢?他們的感受又是如何?從那個時候到現在,有許多的事情已經改變,這個世界也已經改變了,現在準備跨文化宣教又是什麼情況呢?若有機會,我是否會重來一遍呢?我的答案:「是的」。
我走進宿舍區的阿爾發房 (Alpha dorm),進入三個房間的玄關,當時我們全家5個人(加上一隻半合法的貓)在受訓的5個月當中住在這裡。我打開中央桌子的抽屜,拉開然後翻轉過來,那裡我用鉛筆寫上沒有人會看到的信息,「Kilroy was here」字跡猶在。「Karsen家5人,Wendell, Joyce, Stephen, Philip, and Rachel 住在這個房屋(1969年6月~12月),他們正準備在前往台灣擔任宣教師」。看到這裡,我的淚水緩緩的流下來,我想起這三個小小孩子的臉孔,他們陪伴我們面對即將到來的未知命運,現在他們也都成年,有些也有自己的小孩了。我也想起年輕的喬愛斯,她在海外的15年中,是我面對各樣挑戰與歷險的伴侶,直到最後她早於1989年因癌症離開我們。
30多年後,當中有25年是在亞洲度過,我知道這是真正的旅行,上帝仍然信實。我知道,這些年間儘管有錯誤已經造成,但是所完成的卻是許多,想到這裡,我的心裡感到愉快。
首頁Home/
本土信徒總檔
/
教會史話總檔
/
宣教師人物總檔 / 外國神父修女列傳
/ 日人列傳總檔 /
原住民信徒
/
諸家論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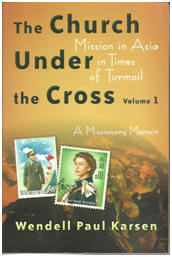 簡介
簡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