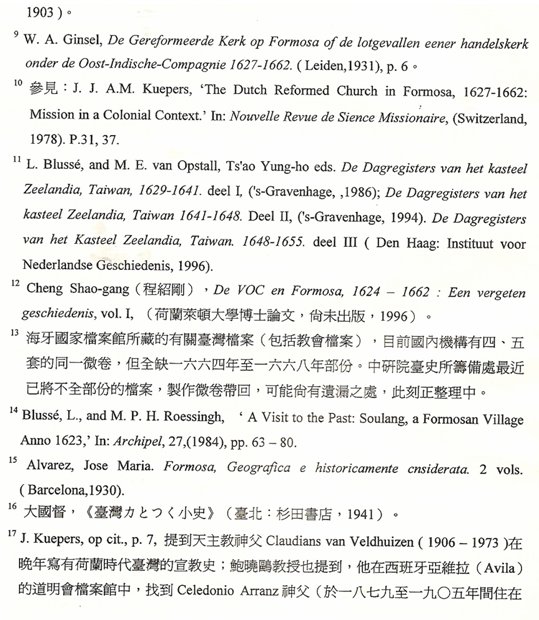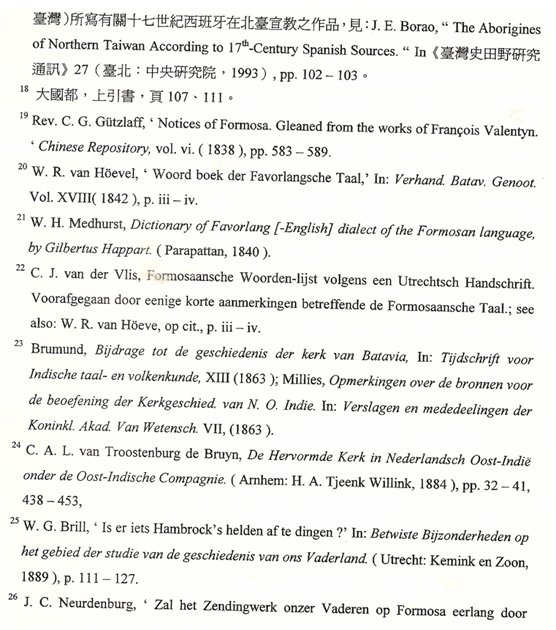|
翁佳音
(待定稿)
原載於《台灣基督教史─史料與研究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宇宙光傳播中心
贊助單位:國科會、教育部、內政部
時間:1998年5月28、29日
地點
台北市市立圖書館國際會議廳
一、前言
二、十七世紀臺灣教會史的資料與檔案
一)西班牙方面的資料與檔案
二)荷蘭方面的出版資料與檔案
三)荷蘭方面未出版的檔案
三、十七世紀臺灣基督教史研究的遺產
一)幾位重要的外國臺灣教會史研究者
二)教會史研究興起的背景
三)研究的學術化
四、研究的課題與展望
一、前言
基督教在十九世紀以前傳入亞洲的歷史,歷來頗受中外學者的注意與研究。不過,關於基督新教傳入華人地區的歷史,就如史家方豪神父所說的[1]:
西洋科學傳入中國是分兩條路線的:一是義大利、葡萄牙等國教士從澳門傳入,因有中國學者接受,並獲得朝廷信任,所以影響較大;另一條是西班牙或荷蘭教士,從馬尼拉、長崎等處向華僑傳佈,程度較淺,所以影響不大,但不能忽視。
亦即歷來的研究重心,是以義大利、葡萄牙的舊教為主。相對的,西班牙、荷蘭的新、舊教在馬尼拉、長崎等處的宣教,比較不被重視。十七世紀的臺灣宣教,正處於方神父所說的另一條「程度較淺、
影響不大」之路線上。
如所週知,歐洲基督新教國家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以來,均忙於解決國內宗派林立之事,無暇如天主教國家一樣,致力往海外宣教。改革宗基督教往外,特別是往亞洲宣教的熱潮,乃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在這種歷史脈絡中,有意思的是,臺灣居然成為十七世紀基督新教在亞洲傳教成功的少數特例[2]。不唯如此,荷蘭人在臺的宣教,對臺灣南部的漢化原住民之影響,亦為研究者所
承認之事。此外,西班牙人在北臺灣宣教的結果,經初步研究,其對臺灣的影響,亦超乎我們所能想像[3]。
因此,不論從教會史或臺灣史的角度來看,十七世紀的臺灣基督教史,都應該進一步加以重視,並繼續進一步研究。以下,本文略微介紹有關十七世紀臺灣基督教的史料,並討論研究情形,最後提出課題與展望。
二、十七世紀臺灣教會史的資料與檔案
既然荷蘭與西班牙的新舊基督教,都同時在臺灣各自傳過教。而且,西班牙在北臺灣的宣教成果,後來為荷蘭人所接收,荷蘭人並在淡水與基隆設立基督教學校。換言之,從臺灣的立場來看,研究十七世紀時期的基督新教史,實不應忽略西班牙的資料與檔案。
一)西班牙方面的資料與檔案
有關基督舊教,即天主教方面在臺灣的宣教檔檔案與資料,其實在二十世紀初,Blair &
Robertson所編譯的55冊《菲律賓群島誌》大套叢書裡,其中已經從西班牙文檔案中,摘譯出宣教士呈西班牙國王的函件、有關北臺宣教的概況,以及當時人所寫的教區歷史,可資初步研究之用[4]。
此外,一些已經出版的西班牙文書籍、方豪神父所介紹的相關資料,仍然值得費神一讀。又,這裡要特別介紹的是,臺大外文系的西班牙人鮑曉鷗教授(Prof.
J. Borao),最近幾年來在我們國內某些單位的支持下,又從菲律賓、西班牙的檔案館中搜尋有關臺灣資料,並有英譯即將出版[5],相信可提供不諳西班牙文的研究者不少方便之處。
我自己也獨立收集這方面的二手資料、論文,並編有書目解題。但我的西班牙語閱讀能力還猶待加強,暫時藏拙為宜,並期待精於西班牙文的國內研究者,特別是舊教的兄姐,能夠早日發表這方面的文章。
二)荷蘭方面的出版資料與檔案
至於荷蘭方面的教會關係檔案與資料,自日本時代以來,已不乏學者專家為文介紹,我不再重複[6]。這裡,我想再談一下大家比較熟悉,而且是重要的資料,即教會史家
胡婁特(J. A. Grothe)所編纂的《舊荷蘭海外宣教檔案彙編O灣部份》。本書的資料來源,主要是從荷蘭海牙國家檔案館中的〈決議錄〉、〈日記〉與〈信件〉等,以及
荷蘭傳統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檔案中,將重要的教會資料,按年份編排出版[7]。此書出版大約十五、六年後,即有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牧師的英譯文刊行[8],為非歐語圈的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若說目前有關十七世紀荷蘭在臺灣宣教史的研究成果,幾乎都是靠甘為霖牧師的英譯本而來,亦非過份誇張之言。
不過,胡婁特在編纂原檔的過程中,仍然遺漏了部份資料[9]。不僅如此,甘為霖牧師的英譯本,亦有若干遺漏甚或誤譯之處[10]。由此可見,今後仍然有必要再收集胡婁特所遺漏的資料,甚至是核對他抄寫編印,以及在後來的翻譯成英、日與中文過程中,是否有關鍵性錯誤之處。
另
外,最近幾年來荷蘭國家檔案局陸續出版的《臺灣日記》[11],也是研究當時教會史與社會、政治方面不可或缺重要的資料,正待有心單位的繼續支持,以及研究者長期
犧牲奉獻,從事出版中文翻譯與註解。目前,巴達維亞城的《總督一般報告》有關臺灣部份,已經有中國的留學生完成譯註工作,國內某家出版社正付梓中[12]。屆時,
對研究荷蘭時代教會史的人而言,將是一大福音,文獻的語言問題已經不是主要的障礙。
三)荷蘭方面未出版的檔案
雖然,將近百餘年來,海牙國家檔案館所藏的資料、檔案陸續被檔案專家編註活字刊行,但仍有絕大部分的原檔仍靜躺於檔案館的書架上,所幸有關臺灣的部分,大多已製成微卷,國內研究者不用風塵僕僕飛往荷蘭調閱與抄寫[13]。當然,海牙國家檔案館中,猷有臺灣相關部尚未被製成微卷者,例如檔案館第一部門(Eerste
afdeling)的私人捐贈收藏檔案中,史威爾(Sweer)、范•柏克豪(Van
Berkhout)家族的收藏文書。尤其是後者,有不少康德(G.
Candidus)與戴雍(De Jonge = R. Junius)兩位重要牧師的信件。這些海牙檔案館的資料,國內目前似仍未有收存。
海牙國家檔案館以外,其他城市的檔案館或機構,亦藏有未出版的檔案,就我目前所知,有:
(一)優特烈賀特國家檔案館(Rijksarchief, Utrecht),其中的海得寇波家族(Huydecoper)檔案中,有幾件有關臺灣的史料。其中一件是大家所熟悉的康德(G.
Candidus)牧師之1628年〈臺灣記略〉報告稿件。十餘年前,該稿件重新被發現,並被介紹於世,我們才得知目前刊行的〈臺灣記略〉之荷文或各種語言的譯文,多有抄錯或譯錯之處[14]。
(二)荷蘭傳統改革宗阿姆斯特丹中會(Archief Classis Amsterdam
van de Nederlands Hervormde Kerk)的檔案。其中有1643、50年大員教會議事會的資料,以及歐厚夫(H.
Olhof)
牧師用新港語翻譯的教裡問答,並附有祈禱文、詩篇(新港語?)。這個檔案雖數量甚少,而且也有研究者引用過,但為資料齊全計,還是有必要抄寫回來。
(三)鹿特丹市立檔案館(Gemeente Archief, Rotterdam)裡的《手稿原件匯集(Handschriften-verzameling)》中,有1652年韓步魯(A.
Hambrouck)、柯來福(J. Kruijf)與哈柏特(G.
Happart)三位牧師寫給阿姆斯特丹中會的信函原件。
這些未出版的檔案,雖然有些是副件,以及有些文件的內容,在其他以及有些文件的內容,在其他的文件或出版資料中可以找到。但製作微卷在國內備存以供核對,仍然有必要的。我老早就想進行,可惜,因其他非學術的人事原因之牽扯,遲遲無法動工。
三、十七世紀臺灣基督教史研究的遺產
一)幾位重要的外國臺灣教會史研究者
約
略再介紹完十七世紀臺灣基督教史料後,我也略談一下研究情形。平情而論,有關西班牙與荷蘭人在臺灣宣教的歷史,至目前為止已經有不少的基礎研究成果,為我們奠定了更進一步的研究。比較為人所知的蘇格蘭基督長老教會的甘為霖牧師,以及西班牙天主教阿耳瓦列司神父(J.
Alvarez)的著作。甘為霖牧師的業績已有目共睹,無庸在本文重提。阿耳瓦列司神父的《臺灣史地誌》[15]倒是值得在這裡一提。該書的第二冊系統性地載有西班牙在北臺宣教的情形,並附有原檔資料的摘譯。可惜的是,國內有關單位在五、六○年代翻譯臺灣史外文研究書籍的過程中,卻漏掉這一本。多年來,我一直找人
合作翻譯與註解該書,但可能是翻譯的事業在學術界不被肯定與支持,所以延宕迄今。
上
述兩位外國人之外,一位日本人大國督所編寫的《臺灣天主教史》[16],亦不應被忽略,該書敘述十七世紀臺灣教會史時,也參考了不少阿耳瓦列司神父的著作。此外,
就我所知,自臺灣重新開放宣教後,有些歐洲宣教士來臺時,本身對歷史有興趣,亦從事整理但並未出版問諸於世,這方面的研究手稿,似乎值得吾人再花一點心思去找尋[17]。
無論如何,上面所述的幾個人之作品,在國內大致可以找到。我底下要補充的是,可能因荷蘭語對大家而言較不熟悉,而一直以為十七世紀的荷蘭臺灣教會史的研究,是由甘為霖牧師開創研究風氣之先,如此一來,荷蘭人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對其失落的海外殖民地臺灣,重新產生研究興趣之事,以及所遺留的成果,恐怕連帶也被忽略了。
二)教會史研究興起的背景
十九世紀之前,天主教雖然曾一再嘗試,企圖重新回到臺灣傳教,但都未能成功[18]。另一方面,如所週知,1803年,基督新教由馬禮遜(R.
Morrison)來亞洲,開展了新教在華人國度宣揚熱潮的序曲。在亞洲有荷印殖民地的荷蘭,因而於1823年左右,由荷蘭聖經公會(Nederlands
Bijbelgenootschap)派遣德人郭實臘(Rev. C. G. Gutzlaff)
前往中國傳教。郭實臘牧師到中國後,於1830年代就注意到臺灣,他還從法連太因(F.
Valentyn)的《新舊東印度公司》一書所記的荷蘭人在臺灣宣教的事蹟,用英文向歐、美人士介紹[19],臺灣曾為基督教國度之事漸為人所知。1850年,郭實臘
牧師回荷蘭,向荷蘭人募捐奉獻支持海外宣教事業,此時關心海外宣教的荷蘭教會人士,已開始注意包括臺灣在內的過去亞洲宣教歷史。
也就在這段期間,1839年,由巴達維亞的牧師侯曄華博士(W.
R. van Hoevel)於巴達維亞(爪哇)改革宗教會檔案館中,找到哈柏特牧師所編輯的虎尾語(Favolang)字典的手稿[20],隨即,先由英國麥都思(W.
H. Medhurst)牧師譯成英文刊行,其後再原件印行[21];符力士博士(C.
J. van der Vlis)亦在此時於Utrecht學院圖書館發現西拉雅的語彙稿[22]。這些荷蘭時代宣教士向臺灣原住民教育的語言資料重新出土,不只重開歐洲語言學家注意到臺灣的南島語系問題,同時也開始正視荷蘭人在臺灣的宣教的事蹟。
對亞洲殖民地宣教史的關心,當然先起於當時爪哇的巴達維亞教會界。其中有Brumund與Millies等人開始從檔案中整理荷蘭人十七、八世紀的教會檔案[23]。1884年,步來殷(Troostenburg
de Bruyn)牧師的《荷印改革宗教會史》一書,便是利用了當時的文章與檔案,討論到當時在臺灣的宣教士事蹟、宣教與語言教育等問題[24]。十七世紀荷蘭人在臺灣的宣教事蹟,此時似乎也引起荷蘭國內的注意,人們開始恢復記得鄭成功圍城時,韓步魯(Hambroek)牧師的英勇殉教事蹟,而且其史事的真偽問題也引起討論[25]。在這種往海外宣教,以及重新回顧歷史的氣氛中,因此有荷蘭教會史家胡樓特(J.
A. Grothe)自1884年前後以降,在本國陸續刊行《舊荷蘭海外宣教檔案彙編》之壯舉。
此時,歐洲方面的
英、荷兩國之新教已合作多時,共同注意殖民地的宣教歷史經驗。臺灣自1865年,由蘇格蘭長老會重新再展開宣教後,亦受歐洲教界的關心。大約1888年前後,知道荷蘭有上述檔案與研究成果的甘為霖牧師返回歐洲,順道往荷蘭到萊頓大學,在語言學家柯倫(Kern)教授的協助下,找出新港語馬太福音的原版。甘牧師並附上英語而重新印於世,他還鼓勵荷蘭人再繼續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26]。此後,甘牧師致力於將荷蘭的教會檔案、資料,如:法連太因的《新舊東印度公司志》、揆一的《被遺誤的臺灣》,以及胡婁特的《海外宣教檔案》等重要作品翻譯為英文,廣向歐陸以外的世界介紹,方便不識荷蘭語的研究者非鮮。
三)研究的學術化
無
可否認,由於甘為霖牧師的熱心介紹,回過頭來也再刺激二十世紀初的學院內荷蘭教會史家的研究。教會史家科衲貝教授(L.
Knappert)因此而寫了〈在臺灣的荷蘭先驅者〉[27]等有關臺灣教會史的小論文。1931年,辛瑟(W.
Ginsel)在他的指導下,完成《東印度商業公司轄下的臺灣改革宗教會史》的博士學位論文[28]。辛瑟是在印尼出生的荷蘭人,後來在萊頓大學讀神學院。他畢業之後,似乎又返回印尼當牧師,我曾在萊頓大學神學院尋找有關他的資料,但僅在一份教會報上看到刊載辛瑟的博士論文出版消息,餘無所得。要之,辛瑟的博士論
文引用了不少胡婁特或甘為霖牧師所未收錄的檔案,而且對當時荷蘭人的宣教史之研究相當有系統性,很期待國內有中譯本的刊行[29]。
至
於其他外國學者新近的研究,由於時間的限制,我希望在會後再補齊。這裡,我想要特別介紹的是一位本土的研究者,即:基督長老教會的退休牧師徐謙信。我個人
以為,雖然自甘為霖牧師以後,並非無本土的有心人士或研究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30],但大體難有新見解的出現。可是,徐牧師值得推崇的原因,在於他把荷蘭時代的教會史,以新教的用語來敘述,使吾人在研讀荷蘭時代的基督教史之時,不至有隔閡之感。而這種工作,我認為應該是目前十七世紀教會史研究的緊急課題之一。
四、研究的課題與展望
除有系統地培養研究生外,我認為仍有如下的基礎工作要進行:。
一,外文檔案中怪異詞彙的註解譯文的核定
雖
然檔案的翻譯與註解工作,在國內學界並未受到應該有的重視與回報。但我還是認為這個工作應該有人來作,讓我們的獎賞放在天上。我姑且舉荷蘭資料中的地名問
題(西班牙資料容另文交代),譬如:著名的「Favorlang教區」,在目前的研究中,幾乎都被譯為「法波蘭教區」。這種譯名,實在無法讓人瞭解荷蘭人
宣教的範圍。其實,此語就是今天的虎尾一帶。
還有,有關教會名詞的考訂等。「疾病慰問師」、「牧師候補」,「評議會」、「中會」與「大會」等的問題,由於曾經日本人的翻譯,我們在戰後又未把他更正過來,使得要瞭解該時段的教會制度問題,格外艱辛。
另外,有些中譯文,可能還要重新核對。我估舉一例,有人引資料云:「普通的中國人十分貧困」,以致有些人「打著赤腳進入教堂」[31]。是誤譯。原意是:規劃漢人不得在拜天赤腳於外面行路。
二,重建事實應優先於歷史解釋
我不得不老實說,雖然十七世紀的教會史研究,有一定的成果,但距離「事實」的呈現,恐怕還有一段距離。我不太欣賞在歷史的建構尚未清明之前,就從事類如「政教關係」,或「殖民政府與教會」等的論述與解釋。
我姑舉幾例:一般以為麻豆神學校只是建議階段,未及實行,可是我指出當時的神學校確實在臺南的蕭(今臺南縣佳里)建立[32];有關西班牙在北部臺灣宣教,目前雖
留存的檔案甚少,幸運的是荷蘭保留有相關的片段情報,可作研究西班牙人傳教的補助材料。從中,我們也可以發現西班牙人在臺的宣教,並不像有些論者所強調的
那樣,都是衝突關係[33]。
另外,目前學界的看法是,十七世紀時,當時西、荷兩國的宣教對象只在臺灣的原住民,但隨著研究的深入,我
們也可看到,在十七世紀之初,漢人基督徒與臺灣歷史有密切的關係!鄭成功之父鄭芝龍(Nicolas
Iquan),李旦(Andrea Dittis)是天主教徒是天主教徒。最近的研究,發現臺灣近代初期史的重要人物,如十七世紀初帶領荷蘭人到中國海域、澎湖一帶貿易,被明朝官方文獻稱為
「海澄奸商」的李錦(Gimpo),他可能是亞洲第一位著名的華人新教信徒。另外,著名的海盜顏思齊(Pedro
China),則是天主教徒[34]。
三,影、抄目前存於荷蘭的有關教會檔案
第二節第三項所提到的荷蘭未出版檔案部份,國內也無微卷,應該有人前往抄製。檔案與資料較齊全,對於研究可能比較方便。例如辛瑟提到檔案中無Masius牧師在北臺灣方面的宣教資料,其實若再深入閱讀檔案,仍可發現有關的資料,這都有待今後的再進一步收集。
四,註釋:
|